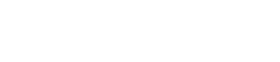|
当高等教育和哲学自觉地认识到自身的局限时,第二十届哲学大会却提出这样的主题——潘迪亚(Paideia,希腊语,有译为“教育”、“人性教化”,人文主义由此而来):培育人性的哲学。这是否表现出一种狂妄、讽刺抑或是实用的乐观主义?哲学怎么可能教育21世纪的人类?在除专业哲学家之外鲜有阅读哲学著作的时代,哲学在哪种意义上能够培育人性?哈佛大学前校长德力克·伯克(1971至1991年任哈佛大学校长)在他的很多著作、文章中曾经提出哲学培育人性的可能方式。伯克坚持认为,美国的一流学院和大学应该再次把道德教育当作自身责任的一部分。
伯克写道:“在19世纪,美国的大学致力于学生的道德发展,并把这归于它们的任务整体中。”伯克观察到,到20世纪中叶,美国学院和大学的课程表上仍旧写着道德是高校经久不变的目标,但是,对这个目标所作的任何努力都已经烟消云散。
在很多情况下,大学把道德教育从核心课程中删除了,关于道德的课程更多地是伦理学的形而上学,甚至那些专心于规范伦理的课程也是在以一种高度抽象的思维方式来讨论道德理论。这类课程的目标是思考权力,而不是塑造公民的美德。我们怎样理解这种变化?
对伯克来说,高等教育目标的这种变化之所以发生是因为:第一,在这些学院中,实用道德教育的理论假设是,由达尔文进化论决定的科学和宗教的最终统一。第二,在“新的知识背景”中诞生的现代研究型大学,其特征是依赖科学和“更加客观的研究方法”。第三,伴随着对专业化的不断强调,出现了学科及其分支,产生了大学生的专业课程。第四,美国经历了从大规模的农村和农业社会向大规模的城市和工业社会的转变,这种社会转型破坏了支撑道德舆论的文化和谐,而这种文化和谐曾经在传统大学和学院中体现出来。第五,研究和出版方面的熟练知识和技能成为聘用教师和决定任期的基本的、经常是唯一的标准。因此,在美国现代研究型大学和很多学术研究机构中,教授的主要工作是调查数据,传授技能,让学生在多元道德视角中自由发展他们的道德信仰和道德实践。
伯克提醒我们,对实用伦理学的重新关注于上世纪60年代开始,迄今仍方兴未艾,但是,这种新的关注和19世纪大学中的道德教育实践并不相同。今天,道德教育课程的目标是使学生为自身而思考道德问题,而不是努力传授一套道德真理,或者帮助学生对具体的某类事件形成道德价值。这种方法当然是有价值的,但是伯克也指出,它是在冒险,它使学生善于对问题的任何方面进行辩论、推理,但是自己缺少严肃的责任感。这种方式鼓励了道德相对主义。因此,伯克呼吁,这种方式是不完善的,它对我们作出适当的道德行为是不够的。在伯克看来,现代大学的道德教育“一方面陷于教条主义的不幸中,另一方面又在道德相对主义中冒险”。现代大学当前面临这样的问题:怎样把道德推理教育和习惯、案例和劝诫教育结合起来?怎样帮助学生在个人和职业生涯中有坚持道德准则的愿望和意志?怎样能够创造一种严肃的道德教育项目,既避免教条主义又避免道德相对主义?
伯克承认,很少有学院和大学尝试着去解决这些难题。伯克对大学综合道德教育课程提出了一些建议:在学院和职业学校中提供实用道德教育课程;和师生讨论行为规范;公正地履行管理规则;建立坚实的社区服务项目,在应对大学所面临的道德问题时采用严肃的道德标准等。
这些课程的目的是使学生在探索道德问题时更加敏锐,对过去的优秀道德思想更加熟悉,在个人和职业生活中对道德问题能够进行更加熟练的推论。
这类课程将会帮助学生成功面对常见的道德问题。很多问题将会呈现出矛盾性,伯克认为,通过诉诸“几乎所有人都认同的基本前提”,学生将会看到,很多道德问题拥有合理而清晰的答案。这些学生既不会成为道德相对主义者,也不会成为独断论者,不会一味模仿从教师那里得来的教条和价值。(作者单位为美国贝勒大学,杨桂青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