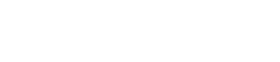转眼间,潘文彬已经在南京市南湖一小任教20余年了。20年前,他绝对无法想到,自己会在这所学校待这么长的时间,会当上这所学校的副校长,会成为最年轻的特级教师。更让他没有想到的是,他会在这里结识三个好朋友:祝瑞松、邢跃武、刘荃。
人生得一知己足矣,何况是三个!
缘分的缔结源于南湖一小,源于他们都是教师,教的都是语文。
熟悉教育界的人都知道,小学男教师很少,小学语文男教师更少了,但是潘文彬、祝瑞松、邢跃武、刘荃却难得在同一个学校教同一个学科,更难得的是他们都对语文教学非常感兴趣,并做出了一番成绩。由此,好奇者有之,羡慕者有之,谈论者有之,更有媒体专门采访了这四个男教师,称之为“M4”,即“4个男人(men)”。当然,除了“M4”之外,他们还有一个更响亮的名字“四条汉子”。
响亮名字的背后,是他们平淡却充实的成长过程。
“四条汉子”是烟熏出来的
潘文彬,1966年生人,1986年来到南湖一小。
邢跃武,1968年生人,1990年来到南湖一小。
刘荃,1973年生人,1991年来到南湖一小。
祝瑞松,1973年生人,1994年来到南湖一小。
除了刘荃是南京本地人,其他三人都来自外乡,天南地北四个人,怎么就聚到一起?原因在于当时的南湖一小是配合建邺区的新兴住宅区而建立的新校,急需老师。这四个人都是师范一毕业就来到了南湖一小。潘文彬是四个人中的老大,一不留神就成了学校的元老级人物。
但是,最初的几年,“元老”的生活是痛苦的,因为寂寞。偌大的学校,老师本来就不多,男老师屈指可数,更别说是教语文的男老师了。老师们多是南京本地人,下课放学后,回家的回家,投亲的投亲,只有这个单身汉住在宿舍里,没有电视,只能靠看书打发时间。
有这种想法的不仅是潘文彬,还有后来的邢跃武、祝瑞松。
寂寞给人带来折磨,但也让志同道合者聚集在一起。盼星星,盼月亮,邢跃武、刘荃、祝瑞松来了,潘文彬终于找到了自己的伙伴。
人家是“焦不离孟,孟不离焦”,他们是整天待在一起,研究怎么上好课。久而久之,这四个人成了学校的常住客。
徐志摩说,牛津的学生是被教授的烟斗熏出来的。“四条汉子”的聚会同样少不了烟,喷云吐雾间纵论天下教育大事,激烈辩论中探讨如何上好语文课,成为他们的重要节目。这是工作,同样也是一种愉悦的休息。每个人都感到交锋的快乐,表达的自由,成长的喜悦。这个类似沙龙的“读书会”一直持续到现在,只要潘文彬一声令下,其他三人无论身居何处,都齐齐赶来,拿着“老大”扔过来的烟,开始赴一场思想的盛宴。
一堂堂好课是磨出来的
烟不是白抽的,成长不仅体现在思想中,更体现在教学实践上。
成长最迅速的是刘荃。1992年,校长燕钜霞来听刘荃的课,一堂课下来,着急得不得了,当时就对潘文彬说:“这个老师上课怎么这个样子,有气无力的,算了,别上语文,教教自然吧。”但就是这个让燕钜霞头痛的老师,4年之后上的一次作文课却艳惊四座,震了所有人,包括区教研员在内。
现在的刘荃,凡是区里需要上示范课,就得作为典型现身说法。每一堂课后,无数的“粉丝”蜂拥而上,用燕校长的话说,“我们的小刘荃课上得‘活’,就像开演唱会,很有轰动效应的。”
刘荃的每一点进步中,自然离不开他自己的顿悟和努力,同时也离不开另外“三个汉子”的帮助。尤其是老大潘文彬,他们是朋友,更是师生。
不仅仅是刘荃,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我们每一次上课都是磨出来的。”这是四个人的共同感受。上课前,拿到题目,每个人都就如何切入、如何设计提出意见,一个思路不行,再换一个思路。然后主讲者将这些意见吸收进来,第二天继续讲课,然后继续提出意见。如此反复,直到把课讲透为止。一个人上课,其余三个人比讲课者更忙碌,更辛苦。上一堂成功的公开课需要准备多长时间?刘荃的回答是:至少一个月!
提起讲课,祝瑞松喜欢一个人对着黑板,反复演练;刘荃则爱琢磨,把自己想象成学生,设想如何提问,如何回答;邢跃武善于在课堂上与学生沟通,了解他们真实的想法;潘文彬说,没有精心的预设,课堂就不会出彩。只有多想象,为一个教学环节设计无数种预案,准备几套方案,课堂才能灵动起来。
一天,一名教师来找潘文彬,让他指导一下自己的教案。潘文彬看了看,说:“先不说别的,你把刘荃老师的教案拿过去看看,他的教案至少有五六页,你只有一张纸,根本就没有下功夫去仔细研究。”
在别人看来,不就是上课嘛,但是在四条汉子看来,上课容不得轻视怠慢,这是安身立命之本,是对学生的负责,更是对自己的负责。
当满大街的少男少女在追“F4”这颗星的时候,南湖一小的“M4”冉冉升起了。南京市建邺区小学语文教研员高文琴老师——这位曾经手把手教潘文彬如何上课的老教师,第一个叫响了“四条汉子”的称号,并且广而告之,逢会必讲。更多的人开始对这四个小伙子产生了兴趣。
多么难得,万花丛中四抹鲜绿,没有变成红花的陪衬,反而愈来愈鲜艳,有盖过红花之势。建邺区甚至南京市的教育局都知道了“四条汉子”的大名,燕校长至今记得,区里领导长听了“四条汉子”的公开课,笑得嘴巴都合不拢。
2001年9月,潘文彬评选特级教师,别人两次三次通不过,潘文彬倒是暴了一个意料之中的冷门,一次就通过,成为当时南京市最年轻的小学语文特级教师。
合作精神是好氛围酿出来的
有人说,一个中国人是一条龙,三个中国人是一条虫。关于中国人欠缺合作精神一说早已有之,但是,“四条汉子”偏偏就打破了这个说法。
原因不仅在于“四条汉子”的感情好,还因为他们有一个好校长——燕钜霞。
虽然已经向很多人讲过“四条汉子”的故事,但是每次重新提起,燕钜霞还是满脸的兴奋:这四个人更像是她一手发掘出来的瑰宝,是她辛苦培养出来的孩子。有什么比母亲看到孩子有所成就更快乐的呢?
潘文彬是这个学校的元老,是这个学校唯一的特级教师,荣誉无数。但燕钜霞看在眼里的是他的好学和谦虚。面对记者,她恨不得把潘文彬的好一股脑全部倒出来。
她说,她没有见过像他这么爱学习的人,到哪里都拿着书。他不仅自己学习,还带领所有的老师去学习。新课程改革,别的学校还没有启动,他们已经在潘老师的带领下开展起来了。
她直言夸赞:“潘文彬是建邺区最优秀的特级教师,但他从来不以特级自居,他把自己所有的才华都贡献给了课堂和学校,他是真正喜欢教育的。”
她有时也“妒忌”潘文彬,因为老师们都很喜欢他,敬佩他,他的人缘好得不得了。每次评先进,民意测验,潘文彬的统计票数永远都是最高,不服气都不行。
谈起邢跃武,她看到的是他对学生的热爱,夸他天生就是一个优秀班主任的材料。她说,邢跃武的字写得真是好,像钢板刻出来的,他们班上的学生都给训练出来了;邢跃武的课讲得很不错,并且他很善于与人沟通交流,善于表达自己。
说起祝瑞松,她毫不掩饰自己的喜欢:“他天生就是一个做领导的材料。”祝瑞松当学生时就是学生会的干部,当教师后充分发挥了这方面的才能。他很会管理,组织能力非常强。“比如搞一个活动,只有祝瑞松能调动起80%的人的积极性,他会写出一个方案,有条有理。当然,他是个完美主义者,如果事情有一点不完美,他就会不开心好几天。”燕钜霞笑着说。
最后说到刘荃,她想起了最初他给她的坏印象,但后来却有如此成就。燕钜霞开心地说,这个孩子,以前是找不到门路,现在是感觉太好了。更神奇的是,一到正式上课,他就气势磅礴,比试讲时效果还要好。
“四条汉子”的故事,燕钜霞讲得眉飞色舞,好像三天三夜都讲不完。
按照人们的一般理解,校长都愿意自己是学校里的代表人物,怎么会避开自己,大讲特讲别人的优秀事迹,并且如此开心,不怕他们“功高盖主”?
而燕钜霞只觉得自己无比幸运,因为有了这四员大将。学校创建10年,都是由潘文彬写汇报材料,校门口每增加一块牌子,都是潘文彬的功劳。怕别人带毕业班不放心,潘文彬就带了10年的毕业班……“无论给这四个人什么任务,只需要简单说明一下意思,这四个人从来不推,并且完成得非常出色。你说,我不是一个非常省心的校长吗?怎么会害怕他们‘夺权’?”
谁说人一多,事情就比较麻烦。燕钜霞以身作则,做了一次人际关系的完美实验。不仅仅是四条汉子,别的老师,只要有潜力和愿望成为好教师,谁都可以去争取诸如进修、公开课的机会。
上课上好了,大家都开心;只有大家合作,才能发挥自己的特长;整个团体好,个人才能发展。这是燕钜霞的理念,也是整个南湖一小的氛围。面对四条汉子的成就,没有一个老师不佩服。而要想迎头赶上,就得靠自己努力,这是学校传递给他们唯一的信息。
四条汉子走了,六朵金花来了
“四条汉子”出名了,挖角的人也多了。2000年,建邺区教育局就开始和燕钜霞商量,要调离四条汉子到其他单位。但是燕钜霞就是不同意,一个都不能走。虽然这有点自私,但她觉得自己就是老鹰,要保护这些小鹰。
2004年,随着燕钜霞的调离,四条汉子不可避免地要分开了。留下,是一个温暖的氛围,走出去,是另外一个未知的宽广世界。
最终,几经周折和坚持,潘文彬继续留在了南湖一小,祝瑞松去了后来的奥运小学做了校长,邢跃武来到区教研室做了语文教研员,刘荃在另外一所学校当了副校长。从区教育局的角度来看,这不是拆开“四条汉子”,而是把优秀的人才送到更需要的地方,他们不仅仅是南湖一小的精英,更是建邺的精英。
走出去的人把南湖一小的团队理念和和谐氛围带走了,留下的潘文彬开始筹划起新的团队。新的“F6”——6朵金花(flower)诞生了,刘宁霞、周爱芳、陈峤赜、李华、黄卉、杨婧成为南湖一小的六朵金花。她们的指导教师就是潘文彬。
燕钜霞走的时候,六朵金花只是嫩芽,两年之后,她们已然是亭亭玉立了。
六朵金花中,有年纪稍长的老师,如刘宁霞、周爱芳、陈峤赜;也有二三十岁的年轻老师,如李华、黄卉、杨婧。不管教龄多长,当她们进入到“F6”的团体后,就开始体验到前所未有的成长。
“以前,我也想,也思考,但是都没有留下足迹。”陈峤赜老师这样评价自己。当真正进入“F6”之后,“师傅”潘文彬不断加压施力,让她们开始自我总结,自我评价,并落实到文字上。
每个月定期聚会,讨论近期所读书目,交流教学心得……“F6”继承了“M4”的传统:磨课。从来不红脸的“闺蜜”们可以为一堂课吵得不可开交,争论到晚上11点钟;很少写教学心得的老师开始思考自己上课的得失;一个人上课,5个徒弟加一个师父磨,得出的经验不可谓不多。
没有压力就没有成长,当她们真正开始留下足迹,真正写出东西的时候,以前的疑惑得到了解答,甚至最头痛的教育论文都不再难写了。
如果说,以前的“M4”更多的是男性的激情,那么现在的“F6”则有着更多女性的细致。她们在用另一种方式抒发教育情怀。
“F6”的集体亮相是在2005年6月16日南京市“发挥名师优势,打造教师群体”现场会上,6朵金花走上讲台,朗诵了自己的教育诗篇,她们每个人都是一朵花。刘宁霞是诗意的茉莉,周爱芳是开不厌的月季花,陈峤赜是素雅的康乃馨,李华是平凡的满天星,黄卉是幸福的向日葵,杨婧是清丽的荷花。
这些花儿该如何绽放,我们拭目以待。
后记:
此次采访,主要对象是“四条汉子”,而老大就是南湖一小的副校长潘文彬。有好心人提醒:你绕过校长,采访副校长,不太好吧?言外之意,撇开正职采访副职,是不是不太恰当。但是当我面对这所学校的教师时,发觉这个提醒显然是多余的。不论是前任校长燕钜霞,还是现任校长王银燕,都对采访倾力支持。他们不遗余力地推出校内的优秀教师团队,自己甘居幕后,为“M4”、“F6”的点点成绩而欣慰。
潘文彬被人形象地称为“潘特”,无论校长还是同事,都对他的能力信服敬佩,他们给予他的评价是,教学好,业务能力强,人很淳朴。或许就是因为这淳朴,他才可以上出好课,就是因为这淳朴,他才会留在这样一个同样淳朴的环境里。
教师是辛苦的,但是如果他能生活在一个单纯的环境,能认认真真地教书,快快乐乐地育人,他体验到的幸福就不是普通的成就感能代替得了的。所以说,“四条汉子”是幸运的,因为遇到彼此,因为来到南湖一小,因为遇到一位好校长,因为得到很多老教师、老教研员的帮助。
而现在,他们把这些心得和快乐继续传递给自己所在的学校。南湖一小有了“F6”,祝瑞松所在的学校有了“七色花”和“四架马车”,他们尝到了团队建设的甜头,也要推而广之了。据说,别的区也在学习模仿中。
从哪个角度看,这都是好事一件。